沈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卢林先生浅谈《万岁通天帖》
 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“又见大唐”展览中又一次见到了倾心仰慕的唐摹王氏一门书翰的《万岁通天帖》,屡见如新,每有收获。虽说是唐摹本,但由于是武则天亲笔书与王方庆(墨制问方庆)求王氏书法,下诏“遂尽摹写留内”,原物赐还。因而这“留内”摹本必为精良,所谓“下真迹一等”者,真迹平生未见,几乎如睹原物。
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“又见大唐”展览中又一次见到了倾心仰慕的唐摹王氏一门书翰的《万岁通天帖》,屡见如新,每有收获。虽说是唐摹本,但由于是武则天亲笔书与王方庆(墨制问方庆)求王氏书法,下诏“遂尽摹写留内”,原物赐还。因而这“留内”摹本必为精良,所谓“下真迹一等”者,真迹平生未见,几乎如睹原物。
现就《万岁通天帖》中王羲之《姨母帖》、《初月帖》和王献之《廿九日帖》谈一谈几点感受:
一、从《姨母》、《初月》二帖中体味王羲之的学书脉络
孙过庭《书谱》中有“羲之云:顷寻诸名书,钟张信为绝伦,其余不足观。”又云“吾书比之钟张,钟当抗行,或谓过之。张草犹当雁行。然张精熟,池水尽墨,假令寡人耽之若此,未必谢之。”(语出晋书《王羲之传》)可见羲之书取法的二大来源:即取法魏钟繇之隶(即楷书)和汉张芝之草。王羲之少从卫夫人得钟繇正书技法,后改师伯父王廙得众体之法(行、草书),而草书则效法张芝。孙过庭对王羲之的书法评价:“元常专工于隶书,伯英尤精于草体,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。拟草则余真,比真则长草,虽专工小劣,而博涉多优。”这些精典的论述我们都能在《万岁通天帖》中王羲之的《姨母帖》和《初月帖》得到印证。
书法继承,指传肤受,始于蒙童,源于家学。据《琅玡王氏家谱》:王旷妻卫氏,生二子,籍之、羲之。于是定卫夫人为王羲之姨母。卫夫人早寡,携子(李充)投靠王家与姐妹同住合乎情理。所以说王羲之早年从卫夫人学书。王羲之性高傲,不尚清淡。有“东床坦腹”和“告墓誓文”之举,但与“幼好刑名之学,深抑虚浮之士”的李充相友善,李充还是兰庭雅集中的重要人物之一。即是“发小”,又相友善。而卫夫人即是李充之母,又为羲之姨母。史称卫夫人“正体尤绝”。而在书法传承中有“蔡邕传学崔瑷及女蔡文姬,文姬传钟繇,钟繇…传卫夫人”之说。钟繇墨迹仅有《荐季姪表》照片,其余为碑刻,又从同时代的东晋《李柏文书》中“平安”二字,再对比《姨母帖》,可以想象当时王羲之初始学书的氛围和点划用笔的含和收敛,即所谓“一搨直下”的“内擫”笔法。
大凡楷书绝妙缘于才华使然,草书精熟本以功夫熟练。钟繇之辈皆为当时世之精英,伴君虎之侧,下笔必当谨慎,常见书文中有“惶恐谨言”之署。纵览后世书家,例如明代虞集等书,莫不是落墨谨慎,笔笔不苟。但书家才华之奕奕神采毕竟遮拦不住,才情流露于极尽收敛的字里行间。具天然之姿的王義之也就有了与其“抗行”之说。《姨母帖》的珍贵之处就在于保存了王羲之初从卫夫人学习钟繇书法的遗迹,摹本可信,最接近真迹。还有一帖能反映王羲之学章草书的是《豹奴帖》,亦为刻本,用笔墨迹为刻痕所掩。通过对《姨母帖》勾摹墨迹的揣摩,能使王羲之《豹奴帖》等其他类似章草复活,功莫大焉!
当王羲之“始知学卫夫人书,徒费年月耳。…遂改本师”即从伯父王廙学书起,即为变体之始。王廙诸体兼善,按当时习俗推崇钟张,无疑可从《初月帖》中按图索骥,想像张芝连绵草体之蛛丝马迹。从王羲之“张芝临池学书,池水尽墨,假令寡人耽之若此,未必谢之。”和“张草犹当雁行。”这些话来看,王羲之承认张芝等人“十日一笔,月数丸墨。领袖如皂,唇齿常黑。”的功夫,按照王羲之的想法是“非不能也,而不为也。”对于这种书法练习不屑为之。因而有“雁行”之说。
与王羲之其它传本墨迹对比可以看到《初月帖》中的草法即有别于《寒切帖》的字字独立的章草体势(《十七帖》刻本亦如此),又不同于《孔侍中帖》、《奉橘帖》的行楷笔势,也有别于《二谢帖》《得示帖》中行、楷、草的混杂。可以说最近似于张芝草书风神,由于自述功夫不及张芝,因而乏张芝大草的放纵,有张芝的“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”的气象,乏“及其连者,气候通其隔行”的视觉张力。因而也遭张怀瓘之“逸少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”之微辞。
庾肩吾在《书品》中有段论述极经典:“张(芝)工夫第一,天然次之,衣帛先书,称为’草圣’。钟(繇)天然第一,工夫次之,妙尽许昌之碑,穷极邺下之牍。王(羲之)工夫不及张,天然过之,天然不及钟,工夫过之。”把王羲之与张芝、钟繇三者间的“天然”禀赋和“工夫”技法之间的关系一语道破!这些都可以在《姨母》、《初月》二帖中细细地品味出来。
二、从王献之《廿九日帖》中看出王羲之变古为新对当时东晋书风的影响并如何理解对其父云“大人宜改体”这句话?
唐张怀瓘在《书断》中有段记载王献之的话:“献之尝白父云:‘古之章草,未能宏逸,顿异真体,今穷伪略之理,极草纵之致,不若藁行之间,于往法固殊也,大人宜改体。’”后人(元袁裒)又有羲之“内擫”,献之“外拓”之说。今观《万岁通天帖》中王献之《廿九日帖》的笔法体势与其父《孔侍中帖》《奉橘帖》等无甚差异,而前三者又与《姨母帖》《豹奴帖》有今古之别。史载王献之学书之始当为七岁左右,这时王羲之年已四十八岁,王羲之五十九岁去世时王献之十八岁。王献之能对其父说“改体”之言,七岁时说似不可能,十八岁说为之过晚,因而此说似疑。但是从王羲之的《姨母》《豹奴》二帖与后传本墨迹之区别来看,王義之书法确实有一个从钟繇收敛的“一搨直下”的“内擫”转化为“外拓”的草隶相间体势的变化,偶用草书侧锋汇入行书,突破钟隶古体形成欹侧遒媚的新书体。如果献之劝父改体之说成立,那么献之在7岁至18岁之间的某一年越往后的话,其父羲之变法时间段就会越少,这种变法的其间段不会超过十年,而羲之变法从流传下来的各种刻本的摹本来看又确实存在,只能说明王羲之书法的锐意求新求变的能力是多么强大!东晋时人互相淘染,这种新书风可能影响到了王献之,只不过王献之书法与其父之性情差异而略有不同外,大体书风还是一致的。要说献之与羲之有差异,仅仅是与羲之早期的《豹奴》《姨母》不同罢了。而历代人云亦云的羲之“内擫”与献之“外拓”泛泛之言的表面文章使人如堕五里雾中。这也有可能宋齐时期崇尚献之而冷落羲之的缘故。
晋时有江南谚云:“尺椟素书,千里面目”。尺椟多为行书,性情尽露。王羲之等一代书家变古章隶之书为新行草书风,也是由于当时东晋的时风和王羲之性格使然:不习惯于官场束缚,受道教思想薰陶,曾与谢安登城而言:“清谈废务,浮文妨要,非当今所宜。”即有入世的抱负,又有《告誓文》之“止足之分,定于今日。”之遁世之想。因而反映到书法中能潇淡散远,不激不厉。思想深处绝无元常之惶恐蹇顿之困,创造出引领千年不必解释的“尽善尽美”的书法审美新体系。
三、武则天为何不把真迹留在宫中而赐还王方庆?
对比唐太宗命萧翼赚《兰亭》的故事,尤其不解武则天为何不把真迹留在宫中?果然如此的话,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王羲之的真迹了!不至于王方庆后人“诸子莫能守其业,卒后寻亦散亡。”
据《旧唐书.王方庆传》载:“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,嘗访求右军遗跡。方庆奏曰:‘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,先有四十余纸,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,先臣并以进之,唯有一卷现今存。…’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,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《宝章集》以敘其事,复赐方庆,当时甚以为荣。”
又据窦蒙《述书赋并注》云:“…时凤阁侍郎石泉公方庆,即晋朝丞相导十世孙。后墨制问方庆,方庆因而献焉。”墨制者,墨敕也。即由皇帝亲笔书写不经过外廷盖印而直接下达到王方庆处,可见武则天对王方庆的重视程度。关键是下面纪述:“后不欲夺志,遂尽模写留内,其本加宝饰锦缋,归还王氏,人到于今称之。”
武则天作为政治家,政声褒贬不一,贬处在此不必叙,现集褒言数例:
唐人崔融:“宗礼明堂,崇儒太学,四海慕化,九夷禀朔…”
唐小说家沈既济:“太后颇涉文史,好雕虫之艺…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。因循日久,浸以成风。”
中唐时期文学家陸贽:“后收人心,擢才俊,当时称知人之明,累朝赖多士之用。”等等。
按当时情景推测,武则天归还原物于王方庆,也是为后人能举褒词之证,赢得“人到于今称之”的美名。
另外,关于“后不欲夺志”的“志”之本意为何?幸览辽海著名学者艾荫范先生大作《“德”在上古文献中的“志向”义———兼与伦理史家切磋》,据艾老考证,“志”与“德”通,并且“志”“德”互文。艾老把“德”字从伦理的角度梳理头绪,举出大量的文献典籍为例证,指出它的主要含义并不仅仅是后世那些属于个人的优秀品质,而且还是维系氏族部落生存发展的一整套的社会规范、秩序、要求、习惯等非成文法规。如《礼记.中庸》所说:“夫孝者,善继人之志,……”秉先祖之德就是继先祖之志。王方庆家藏祖先墨迹前已献于太宗,仅留此一卷以具怀祖之德,而武则天“不欲夺”方庆之“志”,其意似乎在此。只可惜方庆后人其志难继,致使墨宝亡佚。
最后这点仅为臆测猜想,实为浅陋,聊博一笑耳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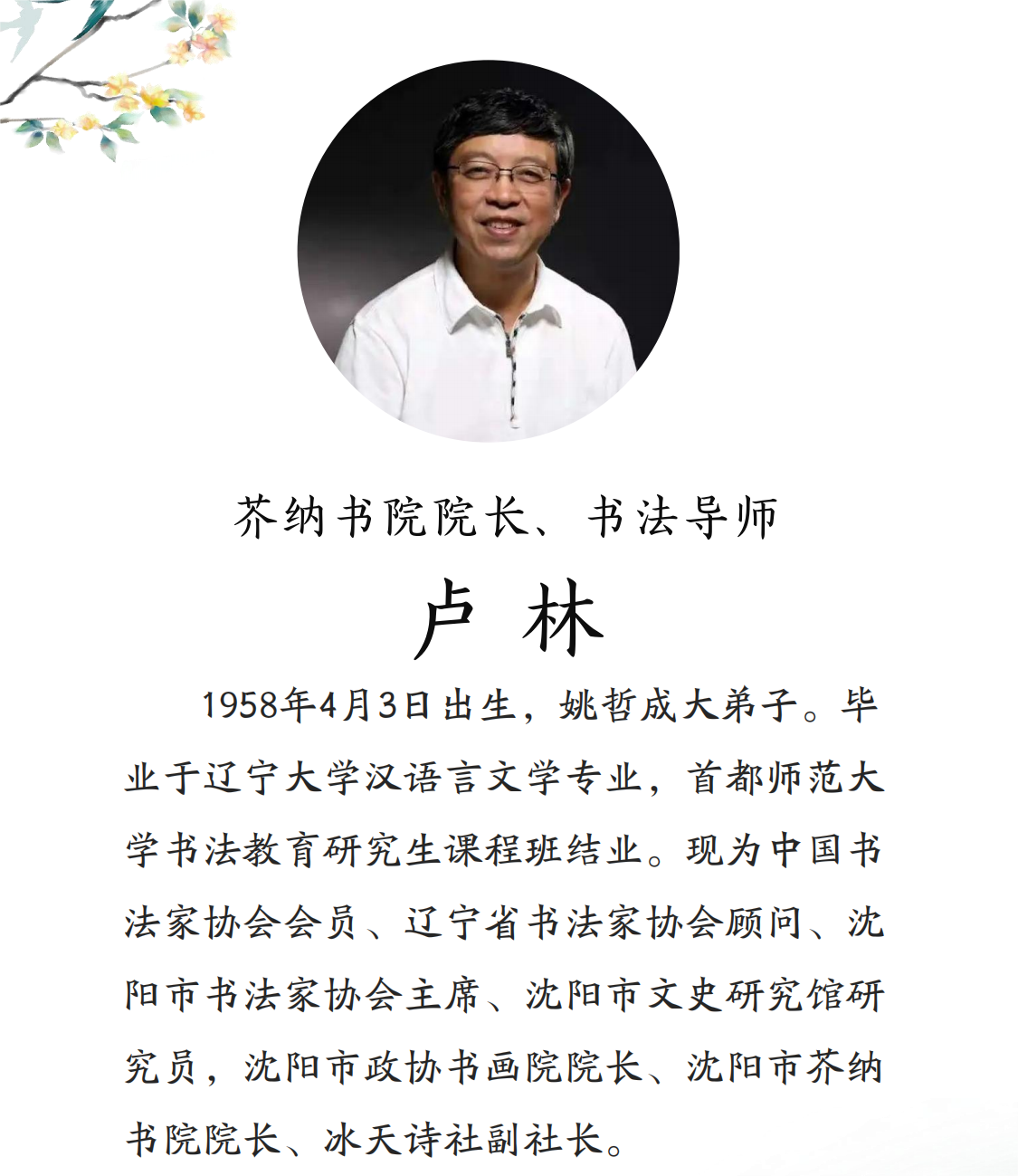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请先 登录后发表评论 ~